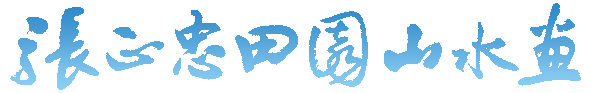
 张正忠作品陈列展 研读张正忠的艺术
张正忠著述快照 走近画家张正忠 田园风光采风 点击张正忠信息 |
《中国田园山水画史》正文摘录六则 唐 王维 王维(701年-761年)字摩诘。唐代诗人、画家。名字合之为维摩诘,维摩诘是佛教中一个在家的居士。开元九年(721年)中进士,任太乐丞,因伶人舞黄狮子受累,贬为济州司仓参军。张九龄执政,擢为右拾遗,又迁监察御史。开元二十五年奉命出塞,为凉州河西节度幕判官。此后半官半隐居。安史之乱被捕后被迫出任为伪职,战乱平息后下狱。后因弟王缙削职赎兄,得到赦免。官至尚书右丞。 王维《辋川图》卷 (宋郭忠恕摹本)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故宫书画图录 十五卷 第195页 绢本、设色, 纵29厘米,横490.4厘米,由清代养心殿石渠宝笈著録。画上有款为“郭忠恕摹本”,卷前有隶书“王摩诘辋川图”6字,收传印记齐全。 王维《辋川图》卷郭忠恕(?-977)摹本,是王维《辋川图》众多临本中最权威的。从许多临本、发展本中比较观察,可以肯定郭忠恕的摹本是忠于原作的,它被编入《石渠宝笈》时列为上等一。元冯子振在附记中说:“海南金元师出此图,与予三十年前张有子家观右丞真卷,无不似。昔者忠恕殆神仙者流,信名下无虚也。”王维与郭忠恕的出生年代约相差200年,是同朝人,能见到真迹,绘画水平又很高,是有可能临摹得接近于原作的。 王维生前在政治上受到挫折,后常隐居辋川山庄别墅。此卷画面群山环抱,树林掩映;亭台楼榭,古朴端庄。别墅外云水流肆,舟楫过往。在王维的山水画中,尤其这幅《辋川图》所创造的悠然淡泊、超尘绝俗的意境,给人精神上的陶冶和身心上的审美愉悦。这是一个丘陵区,山中有若干平地可供建筑宅园。从图中可见到21个景点,它们是:孟城坳、辋口庄、华子冈、文杏馆、斤竹岺、鹿柴、木兰柴、茱萸沜、宫槐陌、临湖亭、南垞、欹湖、柳浪、栾家濑、金屑泉、白石滩、北垞、竹里馆、辛夷坞、漆园、椒园,足见是一个面积庞大的官僚地主庄园。其中辋口庄是主体建筑群,比较豪华。其它处所比较简朴,或接近于田园风光。我相信王维《辋川图》的确是这样的。回顾王维的《积雨辋川庄作》中“漠漠水田飞白鹭,阴阴夏木啭黄鹂”,《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》中“倚杖柴门外,临风听暮蝉。渡头余落日,墟里上孤烟”的诗句,我们曾为诗中美丽的田园景色而陶醉。而他的辋川图中,这种诗意的田园美却非常淡薄,猜想他是如实写生、据实构图,用旅游图的格局来展示实景。图中的画面,并非像诗中那么美,可见他的诗,并不是完全从辋川庄中体验到的,而是他的所见所闻加上理想的成分而构思出来的。为此我一度认为王维的《辋川图》不是田园山水画。后来古代的山水看多了,觉得田园山水画的初期之时,不能以当代人的标准来衡量,而要放宽许多。只要他画了田园景色,就很不容易,所以我称古代的这些画为“中国古代乡村题材绘画”,它是田园山水画的前身,或者说在形成的过程中,通过这个过程慢慢走向成熟。 王维如实反映了辋川庄别墅的景色,给我们提供了翔实的可视形象,虽然缺乏诗的意境,有点“旅游图”的味道,山岺也比较多,田园味不浓,但他的主体还是描绘田园风光的。主旨是隐居山林,即使是山区的村庄,无论其豪华与简朴,我们都可视为田园景色。所以从历史的角度,《辋川图》应该作为萌芽期田园山水画列入,并且是一幅重要的作品。 《辋川图》卷的后人临本选(局部): 佚名唐人 摹《辋川图》卷 日本圣福寺藏 中国山水画全集(上) 第7页 元 唐棣 临《辋川图》卷 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 中国绘画总合图录 续编 第三卷 JM11-170(2) 第22页 明 文徵明 临《辋川图》卷 畏垒堂藏 中国绘画总合图录 续编 第二卷 S24-027(2) 第68页 清 于敏中 临《辋川图》册 私人藏 中国绘画总合图录 续编 第二卷 S19-013(4) 第43页 五代•南唐 赵干 赵干,生卒年不详,江宁(今江苏南京)人,五代南唐画家。后主李煜朝 (961-975) 为画院学生,稍迟于李成,笔法受李成影响。李煜十分爱好书画,其时宋朝已建,南唐称臣苟安,但依然设立画院。“学生”,系画院内的一个官位。传世作品《江行初雪图》的确体现出了皇家画院的细腻工致。据说他善画山水、林木,长于布景。从小生长在江南,故所画山水多为江南一带景物,多作水村、渔市、楼阁、舟船、花竹,具有田园情趣,表现“烟波浩渺、风光明媚”之山光水色尤具独到。李煜降宋,而赵干则矢志不降,以后就未再见他有作品留下来。 赵干《江行初雪图》卷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故宫书画图录 十五卷 第153页 绢本、设色,纵25.9厘米,横376.5厘米。前隔水有“赵干江行初雪图”7字、乾隆弘历题诗,图右边缘有传为李煜的行书:“江行初雪 画院学生赵干状”,[35] 无作者款印。五代时期,画家尚无在画上题字的习惯。图中有“神品上”三字,钤有元“天历之宝”玺、“柯九思印”印、金“明昌宝玩”印,押缝有明“御府宝玩”、“内殿珍玩”、“群玉中秘”三玺及清“乾隆御览之宝”、“嘉庆御览之宝”和收藏家安岐藏印三方、梁清标藏印五方,以及其他收传印记、题跋。此卷历经宋元明清各朝内府及私人收藏,是件流传有绪的精品。 清弘历在前隔水题诗:“吳头楚尾沧江清,元冥试令飞初霙。驴背寒客风打笠,江心渔乐舟冲凌。芦腰已折鬚添白,山头乍失髻矗青。或见沙嘴翁举网,尚有舡脣儿弄罾。夫岂皲瘃之不惧,衣食切已劳经营。冰鱼冻蟹入盘活,谁家羊膏佐软烹。造物不啇省如此,对之令人感慨增。瑶机铄綍识美物,传来北宋腾清声。奎章学士丹邱生,一时法眼精品评。烛照意移生栗烈,画时不知呵冻几度方能成。” 《江行初雪图》这幅长卷,画的是江边渔村的渔民们不顾天寒地冻捕鱼情景,反映了渔民艰辛的生活状况。江天寒雪纷飞,朔风呼啸而来。叶落清疏,树木雾笼;江堤小桥,波浪微泛,水乡一派寒冬寂寥之景。 画面上方是江面。水道错落,江渚时现;水边芦苇低垂,岸上林木萧肃。而水面上有许多渔人捕鱼,或撒网,或收网,或拉船而行,或驾舟穿行;或张起縠罾,或于芦棚中避寒、于船上炊食。忙碌着的老老少少,似不在乎于天寒地冻。水中搭建草棚,撑伞以避风雪,儿童面露苦色;甚而涉足水中,寒冷畏缩之状生动感人,令人怜惜。这是当时渔家生活的真实写照。 江岸有缩瑟不前的骑驴行旅之人。苦行于雪林长堤,人驴面目俱有苦寒难行之色。前后有两队行人,主人骑驴,仆人徒步随其后。前组一主一仆,后组两主两仆;主人都戴冬帽、穿厚衣,而仆人则衣衫单薄,缩成一团。渔夫和旅人成为绝妙的对比。画家以利落的线条画出将近30个人,他们的衣着、动态,连神情也细致逼真、生动传神。 树木都是画落叶空枝,偶有霜叶、残柳,都用中锋圆笔,遒劲老辣。树干以干笔皴染,很像后人皴山,画出阴阳向背。芦花以赭墨裹粉点厾。 布满全画的鱼鳞水波纹,尖细绵密,柔中带刚,千笔万笔,无一笔懈怠。虽然画面的主要面积是水面而土石很少,但仍可见五代山水画处于雏形的皴笔。水边的土坡和石块,密布轮廓及结构、纹理的线条。唐代的山水画空勾无皴,五代开始有所发展,轮廓及结构的线作为勾,而将画纹理的线条作为皴。此图的树干上已有皴笔,坡、石上也密布线皴,只是还不能清楚地名其状。小丘及坡脚,也以淡墨点染而无皴笔,与后来成熟的山水不一样。 尽管石法尚不成熟,画中运用了水墨浅绛技法,树法、芦法、水法、人物画法很成熟,继承了晚唐山水的创作方法,又有了新的进展。用笔方硬劲挺,笔法生动活泼,气韵苍润高古;人物形象生动,树石笔法劲健,水纹纤细流畅,天空以粉弹出雪花,表现雪花轻盈飞舞入水即溶的情景,总体看来技巧十分娴熟。 此画一片自然风景,水乡风光,意境高雅、幽远,见之如身临其境。这样人物与场景完美结合的大手笔,使我们联想到《清明上河图》的气象。他不依靠崇山峻岭、嶙峋山石的意象来构图,而以宁静的渔家生活为主体。虽算不上典型的田园山水画,也是地道的村野景色。此图为赵干仅有的传世作品,是现存最早的无争议的村野之景真迹,一件难得的中国绘画珍品。赵干的这件作品,标志着田园山水画开始进入成熟期。 此画有三点值得注意。 一. 赵干是画院学生,在皇帝身边过着优裕的生活。他在出行的时候,看到了渔民生活的一幕。为了生计,他们在凛冽的寒风中坚持捕鱼,感觉到渔民真是太辛苦了。连贵为皇帝的弘历都感叹“夫岂皲瘃之不惧?衣食切己劳经营”。所以富贵人家能享用美味,“冰冻鱼蟹入盘后,谁家羊膏佐软烹?”因此“对之令人感慨增”,[36] 产生了要表现他们的灵感。作者对渔民艰辛生活有着深切的同情,所以它不同于陶渊明之后隐逸、渔乐的情趣,而是少见的“渔家苦”题材,画得如此生动、感人。 二. 江岸骑驴行旅之人有两组共6人,三主三仆。四人组年轻,随从为书僮;右边一人组年纪较大。他们的共同点是瘦人瘦驴,衣服单薄,抱臂瑟缩。他们既非达官贵人,也非贫苦百姓,而是穷酸的知识分子。从他们身上,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影子。 三. 元文宗(1328在位)为这幅画盖上“天历之宝”鉴藏印章,加上“神品上”的评语,足见当时尽管以崇山峻岭为山水画的流行题材,而取材乡村的《江行初雪图》也得到了高度评价,这说明了这类题材诞生后就具有旺盛的生命力。 注: [35]一说为金章宗(1168-1208)所题,似不大可能。 [36] 见于清高宗弘历在画首的题诗。 南宋 马远 马远3 《西园雅集图》卷 美国威廉罗克希尔纳尔逊美术馆藏 中国绘画总合图录 第一卷 A28-003 第304、305页 绢本、淡设色,纵29.3厘米,横302.3厘米。 西园,是北宋驸马都尉、著名诗人、书画家王诜(字晋卿,1036-1093后,一作1048-1104后)的别墅园林。元丰(英宗赵顼年号,1078-1086)初,王诜曾邀请苏轼、苏辙、黄庭坚、米芾、刘泾、蔡肇、李公麟、晁补之、秦观、陈景元、王钦臣、郑嘉会、张耒、圆通(日本僧人大江定基)李之仪等十六人游园聚会,谈诗论文。李公麟为此创作了一幅图卷,米芾作了图记。后于元祐元年(1086)李公麟在赵德麟家又画了一幅。这次文人集会后人称“西园雅集”,堪与晋代王羲之“兰亭雅集”相比。 李公麟的《西园雅集》手卷,主题比较分散,人物中突出苏轼。元祐年间,汴京文人学士们拥戴苏轼为文坛盟主。由于后世画家景仰苏轼等千百年难遇的文坛奇才,纷纷摹绘《西园雅集图》。著名画家马远、刘松年、赵孟頫、钱选、唐寅、仇英、王式、尤求、李士达、石涛、华喦、顾洛、丁观鹏等,都曾画过《西园雅集图》。以致《西园雅集图》成了人物画家的一个常见画题。 李公麟将“西园雅集”画过团扇、手卷两种不同的本子,加以临摹者的爱好、取舍,或仅凭米芾所撰的《西园雅集图记》想象为之,致传世《西园雅集图》有中堂、有手卷、有扇面,人数、段落也各不一致。尽管李公麟原作已失传,但米芾撰的《图记》传了下来。马远离雅集时间不远,应看到过李公麟的原作。但看来他不满意李的画,又根据《图记》创作了《西园雅集图》长卷。 米元章的记文为:“李伯时(公麟)效唐小李将军为著色泉石,云物草木花竹皆妙绝动人,而人物秀发,各肖其形,自有林下风味,无一点尘埃之气。其着乌帽黄道服捉笔而书者,为东坡(苏轼)先生;仙桃巾紫裘而坐观者,为王晋卿(诜);幅巾青衣,据方几而凝伫者,为丹阳蔡天启(肇);捉椅而视者,为李端叔(之仪);后有女奴,云环翠饰侍立,自然富贵风韵,乃晋卿之家姬也。孤松盘郁,上有凌霄缠络,红绿相间。下有大石案,陈设古器瑶琴,芭蕉围绕。坐于石磐旁,道帽紫衣,右手倚石,左手执卷而观书者,为苏子由(辙)。团巾茧衣,秉蕉箑而熟视者,为黄鲁直(庭坚)。幅巾野褐,据横卷画归去来者,为李伯时。披巾青服,抚肩而立者,为晁无咎(补之)。跪而作石观画者,为张文潜(耒)。道巾素衣,按膝而俯视者,为郑靖老(嘉会)。后有童子执灵寿杖而立。二人坐于磐根古桧下,幅巾青衣,袖手侧听者,为秦少游(观)。琴尾冠、紫道服,摘阮者,为陈碧虚(景元)。唐巾深衣,昂首而题石者,为米元章(芾)。幅巾袖手而仰观者,为王仲至(钦臣)。前有髯头顽童捧古砚而立,后有锦石桥、竹径,缭绕于清溪深处,翠阴茂密。中有袈裟坐蒲团而说无生论者,为圆通大师。旁有幅巾褐衣而谛听者,为刘巨济(泾)。二人并坐于怪石之上,下有激湍潨流于大溪之中,水石潺湲,风竹相吞,炉烟方袅,草木自馨,人间清旷之乐,不过于此。嗟呼!汹涌于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,岂易得此耶!自东坡而下,凡十有六人,以文章议论,博学辨识,英辞妙墨,好古多闻,雄豪绝俗之资,高僧羽流之杰,卓然高致,名动四夷,后之览者,不独图画之可观,亦足仿佛其人耳!” 历代文人雅集题材的作品不少,但能列为田园山水画的不多。这类画虽然主旨都在“雅集”,但人物所处的环境不一样。除了当时的历史事实以外,作者对环境之“雅”有着不同的理解。画家内心与自然山川的物我合一,使他循着自己的思路去想象、取舍。而马远就想到了田园环境,抑或王诜的别墅真的在乡村之中?总之他的这幅长卷有二分之一的长度是描绘村野之景与仆役人等,而且是放在右段卷首。米芾的《图记》感慨说:“自有林下风味,无一点尘埃之气。”他是追求“清高”的审美趣味。而在马远看来,田园的环境,不正是弥漫着“清”气吗?而这“无尘埃”即“清”的正真涵义,还是米芾说得透彻:“嗟乎!汹涌于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,容易得此耶!”他之所以颂扬“雅集”之举,是想与“汹涌于名利”的行为划清界限,树立一个榜样,劝诫世人勿汲汲于名利。这样,就能得到“人间清旷之乐”。西园雅集、《西园雅集图》及《图记》所反映的思想和审美理念,是很明显的。 后代人都把目光投向长卷左段占十分之一的地方,那里聚集着一批名人。在历史长河中,经常有着许多这样的集会,为什么这次雅集受到如此青睐?因为与会者是名人。因此,崇拜名人的看客们往往忽略了占长卷二分之一的村野之景,在选段的时候被剪去,在论述的时候只字不提,似乎是可有可无的。但是,如果细看画面,会发现这段画是挺丰富的。马远用心良苦地经营这段画面,而非“醉来解衣盘礴间”一挥而就。宽阔的河面上一条小舟正由一名船夫驾驭待发;刚从船上下来的两个仆僮,揹的揹、挑的挑,往宅园走去;船码头有一条小路通往河中之坝;河对岸一组人马:三个仆人赶着一马二驴,均驮着物品;其中二位仆夫肩扛着长长的物件,看来很重,连腰都压弯了;河道通向远方,河岸生有竹树。一脉水流经过桥下宅前,穿过树丛竹园、注入大河;水流旁有游廊,廊下有一仆人在蹲地操作。画的左段有松石、泉水、山坡,一派幽静的山林气象。就在这山林与田园之间,露出一座宅园的一角。这个宅园建筑虽未画出全貌,可以看出比较精致,那就是晋卿王诜的别墅了。 在整幅画中,建筑、山石都处于陪衬地位,水、树、坡岸成为主旋律。人物当然有分量,但占比较小。所以这幅长卷描绘的是田园景物之间发生的故事。而这些景物反过来烘托了人物的精神气质和审美追求。 这种大自然中的高级宅园,我们在刘松年的《四景山水》中见过,但刘松年的主旨是唯美的,是富贵人家别有天地的享受;这卷画也有这样的社会背景,但更强调了文人情趣,内涵更为丰富。另外,《西园雅集图》在取景剪裁方面有比较大胆的突破。在南宋之前,长卷极少采取俯视的角度,上树无梢、下树无根的画法。马远在这一点上比李唐有所超越。 南宋 刘松年 刘松年,生卒年代不详,大约活跃于1170—1210年之间。钱塘(今浙江杭州)人,住清波门外暗门,人呼“暗门刘”。工人物、山水界画,神气精妙。是宋孝宗、光宗、宁宗三朝时的宫廷画家。孝宗淳熙(1174—1189)时为画院学生,光宗绍熙(1190—1194)时为画院待诏。师张训礼(原名张敦礼,宋),张是驸马都尉、哲宗之婿,直接师事李唐,因此刘松年的画也有似李唐,属于李唐画派。宁宗朝(1195—1224),进献《耕织图》,宁宗赐金带。 宁宗之后,投降派理宗、史弥远(1164—1233)当政;理宗之后又是昏庸的度宗(1240—1274)和贾似道(1213—1275)当政,南宋走向灭亡的边缘。刘松年是一位爱国画家,他的思想,在一些作品中可以看出。《便桥图》画了唐太宗(599—649)征服突厥的故事,他希望宋代皇帝也能像唐太宗那样富国强兵,打败侵略者,建立强大的国家。他还画过《中兴四将图》,画的是岳飞(1103—1142)、韩世忠(1089—1151)、刘琦(1098—1162)、张俊(1086—1154),当时都为抗金名将。 刘松年的画法精细清润,他没有发展李唐后期山水画的简化、奔放、水墨淋漓的画风,而是加以收敛,这可能与他学张训礼有关。说他的画名超过老师,可能是事实。南宋画院中,山水画都是李唐画派,他的画也不外如此,不过精神稍异而已。刘松年的山水画对马远、夏圭、梁楷等都有一些影响。他是“院体画”代表画家之一。后人把他与李唐、马远、夏圭合称为“南宋四大家”。存世山水画作品不多,有《四景山水图》、《溪亭会客图》等。其中《四景山水图》最能代表刘松年山水画的面貌。 刘松年1 《春社图》卷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故宫书画图录 十六 第215、216、217页 绢本、设色,纵34.4厘米,横267.5厘米。 卷末款书:淳熙四年(1268年)秋七月刘松年造。鉴藏:嘉庆御览之宝。收传印记:内府图书等8方。 《春社图》可说是一幅风俗画。风俗画本是山水画的一个源头,来自人物画。众多的人物,配以环境,就形成了风俗画。风俗画的发展,一脉还是以人物为主,另一脉人物变小,掩藏于山水之间,就成了山水画。因为主旨是人物的活动,有很大一部分在于田园景物之间,那就成了村野之景——田园山水画了。这幅画正是这样,刘松年意在描绘中国古代民俗活动:社日百态。因为这社日在乡村里最为活跃有趣,所以他就画了乡村,结果成了一幅优美生动的田园山水画。 说起社日,我们自然会想起晚唐诗人王驾(851-?),他的七言绝句诗《社日》形象地描写了乡村社日的氛围:“鹅湖山下稻粱肥, 豚栅鸡栖半掩扉。 桑柘影斜春社散, 家家扶得醉人归。”安居乐业的农家,春社欢宴,万人空巷,待下午日已西斜,方渐渐散去,人们都喝得醉醺醺的尽兴而归。据史籍记载,古代春秋两季各有一次祭祀土地神的日子,叫作春社或秋社。社日是立春和立秋后的第五个戊日,约于春分与秋分节相近。农家人在这天的活动里祈求减少自然灾害,祝愿获得丰收。藉此活动之际,进行难得的集体娱乐活动。在那一日,民众集会竞技,进行各种表演,并且聚会欢宴,热闹非凡。这个节日的欢乐场面,在诗歌和绘画中多有记载。 宋代诗人杨万里也写过关于社日的诗,举两首: 《社日南康道中》 东风试暖却成寒,春恰平分又欲残。淡著烟云轻著雨,近遮草树远遮山。 人行柳色花光里,天接江西岭北间。管领社公须竹叶,在家在外匹如闲。 《观社》 作社朝祠有足观,山农祈福更迎年。忽然箫鼓来何处?走煞儿童最可怜! 虎头豹面时自顾,野讴市舞各争妍。王侯将相饶尊贵,不博渠侬一晌癫! 杨万里也算得上诗人了,但他还是超不过那句“家家扶得醉人归”所选择的情节、时段、情景、气氛来得好。从刘松年《春社图》中我们不难看出,它的整个构思就是出自这句脍炙人口的诗。当然,我们把它作为山水画来解读时,更关注的是它的季节、置景以及所带来的乡村意境。通幅以柳树为主景,奠定了春天乡村的特有韵味;水乡春泛,柳岸上几家村舍掩映树间,人物在其中隐现穿行。春天的生命感,人的活力,跃然于纸卷之上。这样的田园山水画,是后世人永远看不厌、常看常新的。 台北故宫博物元另藏有一幅刘松年的《山水图》,其实也是画春社。两幅比较来看,出自一个构思、构图,人物动态、情节安排也完全一样,只是画幅稍短;细节上如衣服色彩、树枝深浅等多有不同,而且在画卷上部没有中景。可能这是《春社图》的前身,从中可见古代大画家的创作也不是一蹴而就的。一些大作品要多次修改完善,保持优点,增益不足,才能比较成熟。这种严肃认真的创作方法,值得现代人借鉴学习。另外,这幅《山水图》的画题肯定是后人加上去的,说明前人对刘松年以描绘春社为主旨的长卷,他们也是视为山水画的。因此我可以说,它也是一幅优秀的田园山水画。 刘松年无意创作一幅田园山水,那么他为什么成就了一幅田园味浓厚的山水画呢?因为春社活动虽是他的创作动机和兴趣点所在,却必须置于乡村的环境中;正因为他意在人物活动,即入世的情节,他没有必要去大写山峦瀑布,而着意表现乡村氛围,烘托人物的环境。结果客观上形成了以人物去画龙点睛,丰富了田园生活的情趣。从中可以看出,之所以形成一幅好的田园山水,是它具备了在出世与入世之间的本质。致使后人在欣赏解读此画时,很自然地把它看作是清静怡乐的世外桃源生活,一幅优美的田园山水画。 刘松年2 《乐志论图》卷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故宫书画图录 十六 第261、262页 绢本、设色,纵29.7厘米,横249厘米。石渠宝笈初编御书房著录。画卷前有篆书“乐志论”三字。画尾款书:刘松年造。 赵孟頫跋,行书《乐志论》全文:“(常以为)凡游帝王者,欲以立身扬名耳。而名不常存,人生易灭。(优游偃仰,可以自娱,)欲卜居清旷,以乐其志。论之曰:‘使居有良田广宅,背山临流;沟池环帀(匝),竹木周布;场圃筑前,果园树后;舟车足以代步涉之难,使令足以息四体之役;养亲有兼珍之膳,妻孥无苦身之劳;良朋萃止,则陈酒肴以娱之;嘉时吉日,则烹羔豚以奉之;蹰躇畦苑,游戏平林;濯清水,追凉风,钓游鲤,弋高鸿;讽于舞雩之下,咏归高堂之上;安神闺房,思老氏之玄虚;呼吸精和,求至人之仿佛;与达者数子,论道讲书;俯仰二仪,错综人物;弹南风之雅操,发清商之妙曲;逍摇(遥)一世之上,睥睨天地之间;不受当时之责,永保性命之期。如是则可以凌霄汉、出宇宙之外矣,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!’元贞二年七年十日子昂书。”(括号内文字系笔者据原文所校正、之字) 揭傒斯跋:“写图易,图意难。得其意而图之工,吾爱松年此图。于乐志之意,得之良深,图之无不悉也。” 鉴藏宝玺:三玺全。收传印记: 紫芝、金华宋氏景濂等11方。 《乐志论图》是一幅类似桃花源题材的理想画卷。东汉末年有一位哲学家仲长统(179-220年),字公理,山阳郡(今山东省微山县两城镇)人。汉献帝时,尚书令荀彧知其名,举荐他为尚书郎。他写的《乐志论》被记载在《后汉书》中,主要是宣扬消极避世的思想,文辞优美,契合古代文人的清高出世观念和老庄追求宁静淡泊、清静无为、逍遥养生的人生观。他描写的“蹰躇畦苑,游戏平林”、“逍遥一世之上,睥睨天地之间”的田园生活,既是他亲身的体验,也为后世文人引起共鸣。很多画家、书法家反复使用这个题材,如初唐诸遂良、元赵孟頫、明祝允明、文征明、张瑞图、王宠、董其昌等都书写过这个描画美好的世外桃源理想的文辞。 仲长统生活在朝纲不振、战乱频仍、道德沦丧、贫富差距悬殊的东汉末年,有过穷愁潦倒的经历,他的理想,也就是他鼓吹的退隐乡野、不求仕进的思想,他认为这才是规避乱世的最佳选择。在弥漫着黄老思想的汉代,产生这样的思想是很自然的。但是他与陶渊明理想的不同是,他没有陶渊明那样决心自己拿起农具,“晨兴理荒秽”,而是想躲进乡村,“使居有良田广宅”,“使今足以息四体之役,养亲有兼珍之膳,妻拏无苦身之劳;良朋萃止,则陈酒肴以娱之……游戏平林、濯清水、追凉风,钓游鲤,弋高鸿……”这样具有优裕物质保障的地主生活。既避世,又优裕,不劳苦。钓钓鱼、乘乘凉、讲讲书、弹弹琴,好不快乐!这种理想不是建筑在自食其力的基础上,是少数富贵之人才能享用的,因而对大多数人来讲是不现实的。所以后世的苏、米、黄、蔡,这些信仰黄老的大家,都没有唱和他的论调。 当然,刘松年肯定是非常赞同仲长统的观念了,他尽心尽力地画了这幅《乐志论》,艺术性是一流的。内容是完全在阐发《乐志论》的内容,可谓从视觉图像上淋漓尽致地描绘了仲长统的理想图景。卷右第一段:乡村的一隅,小桥流水、杨柳依依,田畴农夫、水中游鸭,蒹葭苍苍、水波悠悠,鸡犬相鸣、儿童戏嬉,一派太平盛世的田园胜境。第二段:在绿树修竹、假山围垣的掩映下,朴素而高雅的厅堂里,主人正在与客人读书论文。一主两客,倒有四个仆人在服侍他们。主人眼睛盯在书上,一只伸出来到仆人端着的盘子里取果子。第三段:在松荫竹柳丛中,侧厢房里是主人的“妻孥”,摇纨扇凝望窗外,“安神闺房”;仆妇忙碌行走,后屋厨房里有妇人在打理膳食,“烹羔豚以奉之”。左侧末段:曲水环绕,小桥通往后花园,篱门里种植花木,筑有幽居;石洞里流出淙淙清泉;一文士在泉中濯足,一书僮服侍在侧;另一书僮肩扛一张琴走来。 全画描绘了一个优雅、富足、平静的世外桃源。这种既无劳苦又无干扰的闲适生涯,是当时士大夫阶层的幻想。一般的隐士,必须承受耕作之劳、断炊之虞、虎豹盗贼之害,并非是那样潇洒舒适的。由于时代的局限,仲长统并未开出什么好药方。但他能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有所认识,便很可贵;总比整天利欲熏心、尔虞我诈、男盗女娼要好得多。另外对于以养性为养生的见解,也有它的道理,他所提出的正是传统的道家养生观。 不过画中主人公的生活理想建筑在逃避社会责任、不劳而获的基础上,这是它受仲长统影响的消极的一面。建筑在这种基础上的养生术并无推广价值。当然我们评价它的这种社会观,不能以今天的认识来苛求古人。 在我们面前的是刘松年一幅优美的田园山水画。它当时的创作主旨是人物活动,但我们看到了田园的宁静、高雅之美,而人物只是点景而已。富人和穷人共同构成了田园的情境,从山水画的角度,它们都是田园景物。浓浓的田园生活情趣来自刘松年构筑的曲折多变的画面,也来自宋代的实际生活。在这里,大自然的赐予与人类劳动的成果浑为一体,既是隐逸的清静之地,也是生活的良好环境。 刘松年3 《江乡清夏图》卷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故宫书画图录 十六 第209页 绢本、设色,纵31.6厘米,横503.5厘米。款书:嘉定元年(1208年)春日制,刘松年。 白珽跋:“宋刘松年初师张敦礼,后遂过之。此江乡清夏图乃松年笔也。苍劲中不乏森秀,古雅处复带鲜妍。诚画院中之首推,宜仲英之珍若拱璧耳。” 钱惟善跋诗:“渺渺晴山路更幽,茸茸瑶草几春秋。岩栖自昔推巢父,学种于今说故侯。云物岂因时序换,鹿蘪不共世尘浮。溪头蓦有寻真客,期向山中汗漫游。” 黄溍跋诗:“绿树沉沉复草塘,湘帘齐揭藕风凉。人间无地逃炎暑,安得移家住上方。” 张羽跋诗:“仙人消夏属林塘。琼馆无尘松荫凉。吟罢当窓日正午。农歌渔唱起遐方。张羽次韵题。” 朱墅跋诗:“苍厓过雨流清玉,万朵芙渠红间绿。松枝摇动碧簾风,兰舟徐度回塘曲。画阁朱楼没翠褕,银牀冰簟上流苏。美人倦绣频来往,僊侣长吟聊自娱。羽扇不挥尘不到,博山麝脑香犹袅。新蝉惊破北窓眠,幽禽啼断林间巧。竹烟浮翠荐龙团,树影当庭映日圆。堪嗟田畔农工苦,谁识高斋六月寒。” 陈继儒跋诗:“山深赤日不到地,树老绿阴高刺天。鹤叫岛池藏怪石,窗撩花户映飞泉。閒翻古帖摹青李,时放轻舟採白莲。君若入山同结夏,北窓松月对牀眠。” 收传印记: 贾似道印、松雪斋图书印、宣文阁鉴书画博士印等10方。 元代文学家黄缙(1277-1357)在《江乡清夏图》的跋诗里有句:“人间无地逃炎暑,安得移家住上方。” 刘松年的这幅画,是一帧田园山水巨作,卷长超过5米,首先给人的感觉是可游可居。特别是那样引人入胜的绿色环境:小舟悠悠、水面空旷,柳荫宅园、田畴水车,茂林修竹、石泉幽静,可谓尽田园美景于一卷,令画外之人羡艳。它的创作主旨,与《乐志论图》的理想是一致的,就是寻求一种比较清雅的享乐养生环境。在今天看来,安居乐业于平静优美的田园之间,是每个平民应有的生活,并不存在着避世隐逸的目的。但是在南宋,像刘松年这样的画家,熟知官宦阶层,并且厌恶他们奢华荒淫无度的生活方式,所以对仲长统的“避世、享乐、养生”的清雅生活理想产生共鸣。在那个时代,能有这样的理想,已经算是难得的清醒之人了。如今,无论它的时代主旨、细节如何,在我们眼里它都具备田园山水画的属性,是当宋代村野之景之无愧的优秀代表作。 在《江乡清夏图》中,不可避免地如实反映了阶级的差异。在柳荫宅院里,富裕的文人在抚琴雅操;美人放下手中的绣品,在风凉的画阁朱楼地来回走动;高朋仙侣在摇着羽扇吟诗自娱;蝉与幽禽的鸣叫声惊醒了在北窗睡觉的妻孥;而此时天气很是炎热,红日当空,庭中绿树投下了日光的阴影。作为同是生活优裕的明代儒家文人、朱熹十一世孙朱墅也在跋诗中感叹:“堪嗟田畔农工苦,谁识高斋六月寒?”在炎日下劳作的农工,“汗滴禾下土”,何曾享受过“高斋”里文人美女们六月炎夏还是凉风习习的生活呢?鲜明的对比处于同一长卷之中,《江乡清夏图》是真诚的创作。他做到了荆浩所谓的“图真”,为我们提供了宋代生活的真实可视细节,堪称“画史”。而在审美的同时窥见人类的生存状态,正是田园山水画这个画目的一个长处。 |